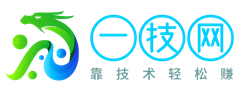上海,始終是女性議題生發(fā)和文藝創(chuàng)新的先鋒陣地。從王安憶、奚美娟到朱潔靜、柳鳴,從袁雪芬、陳薪伊到邵藝輝、周可,一代又一代的女性文藝工作者在這里生長、出發(fā)、閃耀。開放多元、兼容并包的城市文化,不僅給予女性文藝工作者以自由發(fā)展的舞臺(tái),更是她們創(chuàng)造性思維的源泉,同時(shí)也以她們的作品和表達(dá),參與塑造著這座城市的品格。她們以上海為支撐,以文藝為舟楫,引領(lǐng)著我們駛向更為遼闊、更為和諧的文明海洋。
在第115個(gè)國際勞動(dòng)?jì)D女節(jié)來臨之際,澎湃新聞上海文藝推出“伊的藝術(shù)”專題,從文學(xué)、影視、戲劇、舞蹈、古典樂、音樂劇、脫口秀、藝術(shù)展覽等8個(gè)領(lǐng)域,集中呈現(xiàn)近年來上海女性文藝面貌,向全體女性文藝工作者致敬,向她們杰出的工作致敬,向始終致力于各個(gè)領(lǐng)域的性別平等,消除偏見和歧視,致力于加深文明圖景的所有行動(dòng)者、發(fā)聲者、擁護(hù)者,致以深深的敬意。
當(dāng)我們以“女性”作為切入點(diǎn)去評(píng)論文藝作品時(shí),似乎總是會(huì)劃出兩道平行的語境,一方面,正如我們需要婦女節(jié)來紀(jì)念女性為爭取“生而為人的平等權(quán)利”付出的巨大努力,時(shí)至今日,滲透在世界各個(gè)地區(qū)與領(lǐng)域的性別歧視仍舊客觀存在,我們毋庸置疑地需要更多女性創(chuàng)作者和作品,以及圍繞她們的討論。另一方面,當(dāng)性別被置于創(chuàng)作者和作品之前,似乎又造成了一種被觀看、被概念化的效果。我曾在一場(chǎng)電影映后交流現(xiàn)場(chǎng)聽見主持人問女性導(dǎo)演:“您認(rèn)為這是一部女性電影嗎?”——沒有人會(huì)向男導(dǎo)演提出這樣的問題。如戴錦華所言:“這種優(yōu)先考慮性別的方式好像忽視了一個(gè)常識(shí),女性本來就占人類的一半。”于是另一個(gè)常識(shí)也被忽視了,“女性作品”是直指女性的,自然也就直指人性,以及人類社會(huì)。
在戲劇這一領(lǐng)域,這種討論愈發(fā)有意義。戲劇從四百多年前的莎士比亞時(shí)代以來,就是一種以“人”為內(nèi)核的藝術(shù)。戲劇的在場(chǎng)性、互動(dòng)的即時(shí)與不可復(fù)制(如本雅明所說的“靈韻”)又讓其具備了獨(dú)特性,戲劇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劃出一個(gè)沉浸互動(dòng)的時(shí)空,讓我們以最當(dāng)下的狀態(tài)直面關(guān)于人類的各項(xiàng)議題。而在梳理近幾年上海女性戲劇創(chuàng)作者的作品時(shí),一種明顯的趨向浮現(xiàn)出來——女性視角發(fā)掘了一種更敏銳、開闊和平視的視角,啟發(fā)我們看見更全面,也更接近真實(shí)的人類世界。
面對(duì)經(jīng)典:奧賽羅的悲劇不在于他是“嫉妒的丈夫”,而在于他本質(zhì)的不自信
2022年,導(dǎo)演陳薪伊推出了一部“全女班”的《奧賽羅》,這不是她第一次排演這部莎士比亞的經(jīng)典劇作,早在1986年,她導(dǎo)演的《奧賽羅》在上海展演,就引發(fā)了市場(chǎng)的極大關(guān)注,場(chǎng)場(chǎng)爆滿,據(jù)說成為“上海戲劇界多年未見的盛況”。

《奧賽羅》劇照
從第一版開始,陳薪伊詮釋的《奧賽羅》就有明確、銳利的視角。原著中,威尼斯公國的勇將奧賽羅與元老的女兒苔絲狄蒙娜相愛,由于種族身份(奧賽羅是黑人)等原因,婚事未被允許。奧賽羅手下的旗官伊阿古一心想除掉奧賽羅。他向元老告密,卻促成了兩人的婚事,于是開始挑撥離間,并偽造了苔絲狄蒙娜與他人的定情信物。奧賽羅信以為真,在憤怒中掐死妻子,并在得知真相后自刎。在傳統(tǒng)的詮釋版本中,人們將奧賽羅的悲劇歸結(jié)為因嫉妒導(dǎo)致的輕信。
陳薪伊在1986年的導(dǎo)演闡述中寫道:“我對(duì)嫉妒的丈夫形象不感興趣,如果一個(gè)女性優(yōu)秀,沒有一個(gè)丈夫不嫉妒,這不值得進(jìn)入我理解的悲劇。奧賽羅輕信的真正原因,是他本質(zhì)上的不自信。我認(rèn)為苔絲狄蒙娜是太陽,奧賽羅是月亮,是借著太陽的光發(fā)亮的。苔絲狄蒙娜愛著奧賽羅,而奧賽羅認(rèn)為被苔絲狄蒙娜愛著就證明了自己的價(jià)值,這是他的動(dòng)機(jī)。有譯者評(píng)價(jià)苔絲狄蒙娜身上有封建殘余,我認(rèn)為這非常滑稽,苔絲狄蒙娜不是被觀念束縛的,她是真正去愛的人,愛是自信的,她是勇士。”
在2022年的版本中,她繼續(xù)從奧賽羅愛的起點(diǎn)出發(fā),挖掘他的心理動(dòng)機(jī),“苔絲德蒙娜象征著美的信念,奧賽羅的悲劇在于對(duì)他所追求的美喪失了信念。”在奧賽羅決定殺妻時(shí),他對(duì)苔絲德蒙娜說,“我要?dú)⑺滥悖缓笤賽勰恪?rdquo;他渴求的是一個(gè)美麗的死人,一個(gè)確定的、能夠證明自我價(jià)值的私有物品,而活著的苔絲德蒙娜則隨時(shí)可能映照出他內(nèi)在的孱弱和自卑。直至奧賽羅自刎前的宣言,他仍舊在讓人們記住他那些“維護(hù)國族的榮耀”,來掩飾內(nèi)心的空乏和自我價(jià)值的不確信。當(dāng)“全女班”的演繹在視覺上弱化了傳統(tǒng)的兩性特征(及相應(yīng)的刻板印象),似乎也在推動(dòng)觀眾的進(jìn)一步思考——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奧賽羅本質(zhì)上的空乏和不自信?
看見當(dāng)下:那些更隱秘、更復(fù)雜的處境,只有被看見才有可能被改變
過去兩年間,導(dǎo)演周可接連推出了《初步舉證》和《玩偶之家2:娜拉歸來》的中文版話劇舞臺(tái),這兩部以女性為主體展開的話劇擁有同樣鮮明的氣質(zhì),它們足夠當(dāng)下、足夠銳利,也有足夠的延伸性,能與我們的生活產(chǎn)生互動(dòng)——當(dāng)越來越多的女性覺醒了,然后呢?我們?nèi)匀簧硖幰粋€(gè)舊的律法體系乃至價(jià)值體系當(dāng)中(不平等只是變得更加隱秘而從來沒有真正消失),不僅如此,我們也在走向一種彼此隔絕的“原子化”時(shí)代,我們應(yīng)該如何面對(duì)生活,如何自處?
這兩部作品,從編劇、導(dǎo)演到演員呈現(xiàn),都在以真誠開放的方式與我們展開討論。

《初步舉證》劇照
《初步舉證》由蘇西·米勒編劇,2019年首演以來,在全球口碑極佳。在中文版中,主角泰莎是一位出身小鎮(zhèn),靠自己的努力躋身名校的優(yōu)秀律師,她經(jīng)手無數(shù)性侵案,技巧豐富,殺伐果斷,常為性侵案中被控男性辯護(hù)。在一次與男性同事朱利安的約會(huì)中,她遭受了性侵。在選擇起訴后,她承受了身心的雙重傷害。
導(dǎo)演周可分享看劇本時(shí)印象深刻的情節(jié):“泰莎喝多了想吐,她的意愿發(fā)生了改變,但那個(gè)時(shí)刻朱利安沒有聽到這個(gè)訴求,因?yàn)橹炖仓廊绾毋@法律空子,在整個(gè)文本中對(duì)從事法律的人來說,沒有所謂的真相,只有法律的真相。”這也是這部劇的核心意義之一,泰莎作為受害者,不僅在法庭上一次次被揭開傷疤,遭受質(zhì)疑否定,她也被曾經(jīng)深信不疑的律法正義拋棄了,切身遭遇讓她看見了這個(gè)巨大漏洞——被侵害方的真實(shí)反應(yīng)在法庭上是不被看見的,女性被性侵的經(jīng)歷,不符合以男性為主導(dǎo)的正義體系。法庭默許侵害方的“無知”(和假裝無知),而這種無知本身就是罪惡。
泰莎在下半場(chǎng)以近乎嘶喊的真摯表演,向我們展示了被侵害的傷痛,被背刺的絕望,以及面對(duì)真實(shí)、質(zhì)問正義的勇氣。這也與上半場(chǎng)她在社會(huì)成功體系這個(gè)賽馬場(chǎng)中的努力廝殺、意氣風(fēng)發(fā),形成了強(qiáng)烈對(duì)比。這個(gè)對(duì)比殘酷而真實(shí)地揭示了我們所有人面臨的某種騙局,“新自由主義”式的機(jī)會(huì)均等、個(gè)人自由的承諾真的公平嗎?當(dāng)所有普通人在賽馬場(chǎng)上廝殺,以為能夠?yàn)樽约旱倪x擇負(fù)責(zé)時(shí),賽馬規(guī)則本身又是如何制定的?
如果說《初步舉證》是一把利劍,帶觀眾看見隱秘的傷痛和真相,《玩偶之家2:娜拉歸來》則提供了一個(gè)可容納的空間,通過不同的人、不同的立場(chǎng)之間的溝通,看見我們所身處世界的復(fù)雜。

《玩偶之家2:娜拉歸來》排練照
盧卡斯·納斯在2017年創(chuàng)作了《娜拉歸來》,在這個(gè)版本中,易卜生筆下的娜拉在離家15年后歸來,她成為一名書寫女性話題的知名作家,她需要一個(gè)正式的單身女性身份,于是回來找丈夫離婚。這個(gè)版本的娜拉獲得了全球的關(guān)注,和其他續(xù)寫版本不同,它似乎更貼合我們當(dāng)下的真實(shí)處境,女性覺醒了出走了,隨之而來的呢?
周可說:“在我們觀看戲劇的過程中,常常會(huì)習(xí)慣性認(rèn)為女主說的一切都是真理的化身。當(dāng)我們要去尋求絕對(duì)正確的時(shí)候,我們勢(shì)必會(huì)居高臨下,甚至將觀點(diǎn)不同的一方視作需要被修正的錯(cuò)誤的一方。《娜拉歸來》正試圖去構(gòu)建一個(gè)互相聆聽的世界。”于是在這版娜拉故事中,我們聽見同為母親的保姆安娜對(duì)娜拉說:“我們不一樣,你有一個(gè)有錢的父親,而我沒有,你有選擇,而我沒有。”也聽見丈夫托瓦和娜拉的對(duì)話,他們比起易卜生筆下的人物,更像是面臨婚姻危機(jī)的當(dāng)代人,編劇和導(dǎo)演讓托瓦打破了“述情障礙”,與娜拉交流了他15年來的內(nèi)心變化、他的焦慮和渴求。歸來的娜拉也與18歲的女兒艾美展開了對(duì)話,艾美質(zhì)問娜拉:“因?yàn)槟愕臅卸嗌倥穗x開了她們的丈夫?又有多少母親拋下了她們的孩子?這就像你從一艘沉船中救起了所有的人,卻沒法把她們帶上岸,任由她們?cè)诿C4蠛V衅?rdquo;而娜拉的回應(yīng)是:“你覺得我沒有給你任何東西,但是你不知道我給了你什么,因?yàn)槲艺跒槟銧幦。瑸槟汩_拓一個(gè)新的世界,這個(gè)世界尚未實(shí)現(xiàn)。”
在這部劇中,每一個(gè)角色都站在自己的立場(chǎng),但每一個(gè)人都擁有了自我表達(dá)和與她/他人溝通的機(jī)會(huì)。中文版舞臺(tái)演出后,有觀眾質(zhì)疑這個(gè)“和解”式的結(jié)局是一種妥協(xié)和退步。導(dǎo)演周可回應(yīng)說,“盧卡斯·納斯在創(chuàng)作這個(gè)戲的時(shí)候,應(yīng)該深切地感受到了這個(gè)世界的割裂。尤其是在2012年之后,過去那些被推倒的墻又重新被建立了起來,我們時(shí)常會(huì)感覺到強(qiáng)烈的對(duì)立,無論是政治、信仰、種族,還是男女之間。這個(gè)劇本貌似在探討家庭當(dāng)中的矛盾,包括階層、性別、代際的觀點(diǎn)碰撞,實(shí)際最終討論的是這個(gè)世界面臨的共同問題——我們?nèi)绾尾拍軠贤ǎ?rdquo;
這種女性戲劇創(chuàng)作者間的彼此理解也向“原子化”的、個(gè)體彼此獨(dú)立的社會(huì),傳遞出一種穩(wěn)固的力量,她們既看見了自己(和與自己處境相似的人),也希望那些身處絕境的人能夠被看見,不僅如此,那些立場(chǎng)不同的人也應(yīng)該被彼此看見,因?yàn)橹挥斜豢匆姡淖儾趴赡馨l(fā)生。
在我們紀(jì)念婦女節(jié)的此刻,也有更多的女性戲劇正在上演。由上海話劇藝術(shù)中心制作的《蒼穹》中文版,是前不久在上海開演的一部女性群戲,已經(jīng)被很多觀眾預(yù)定為“年度最佳話劇”。《蒼穹》原劇劇本出自劇作家露西·柯克伍德,2020年在英國首演。這部講述18世紀(jì)英國農(nóng)婦生活的話劇,正在21世紀(jì)20年代全世界的劇場(chǎng)里不斷引發(fā)著情感共鳴和震蕩。它是一種微妙的“女性戲劇時(shí)刻”,一種長久存在于暗處的歷史真相浮現(xiàn)出來,撞擊著當(dāng)下的生活真相。《蒼穹》以哈雷彗星的兩次到來作為開頭和結(jié)尾的背景,在結(jié)尾處,哈雷彗星在2061年再次來臨,我們和幾個(gè)世紀(jì)前的女人們一樣,仰頭望向蒼穹,接受著叩問——當(dāng)我們?cè)趹騽≈斜平鼩v史和當(dāng)下的真相,是否能夠一起改變我們共同的未來?